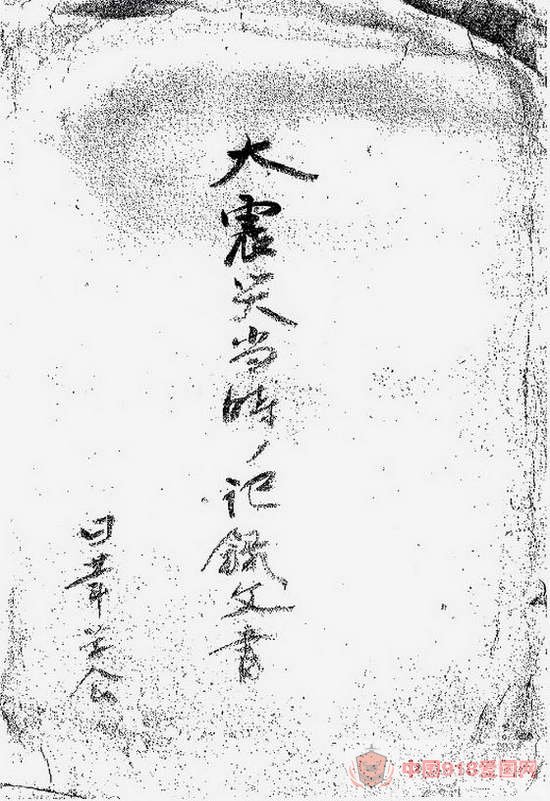日华学会理事 山井格太郎氏的手记
作者:山井格太郎 翻译:朱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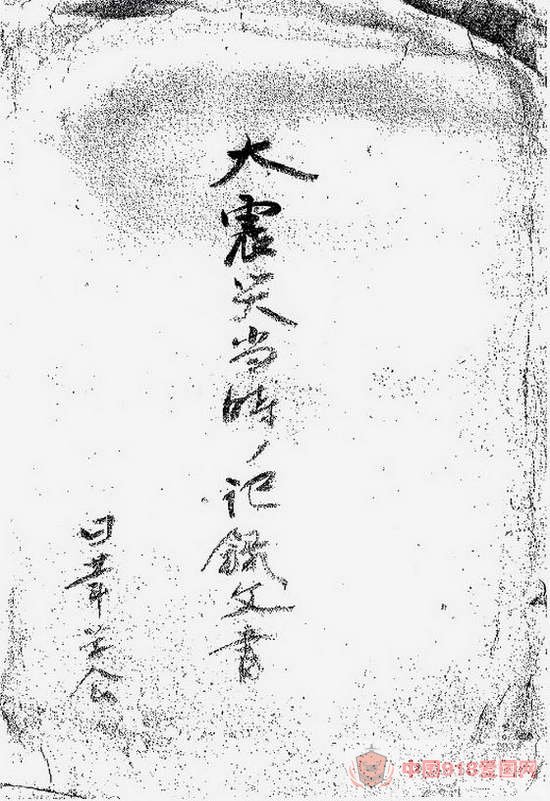
这篇文章写于1924年,但写作日期不明。 抄写者:林叔飙 原文收藏:林伯耀
朱弘注:日華学会是为日本方面为中華民国留学生建立的最大的“接纳组织”,成立于1918年,出头的都是日本社会头面人物(包括前总理和一批贵族),从留学生的学校选择、入学、转学,到宿舍、银行、工厂实习/参观,都起到斡旋的作用,和日本外务省关系极深。作者山井格太郎是该学会理事,后来成为最高理事,以下是他一年后的回忆录。
他的回忆录,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揭示了当年排外主义的严重,以及可以想象的:王希天前往大岛町探望中国劳工(主要是温州、青田人)生死存亡的艰辛。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我只能说:王希天太伟大了!几天后,他在当地被日本军人残忍杀害。
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受难情况
在此,我试图按自己的记忆录下去年大震火災发生之际“日华学会”的工作。
(9月1日)
九月一日上午十时左右,我因学会的有关事物访问了近卫步兵第1联队。归途中,正与三位中华民国人士一起走到丰川稻荷神社前的车站等候电车的时候,大地震发生了。车站前有一家大型陶瓷商店,只见陶瓷制品(锅碗盘碟)伴随着巨大轰响摔落下来,房屋也倾斜了。当时尚未感觉是多大的地震,但随后就发现电车停了,眼前的人们在惊慌中左跑右窜,而附近的顺天堂医院、学校、区公所遭到了巨大破坏,大批伤员被抬了出来,我这才意识到地震相当严重。(略)同行的三位中国人从未经历过大型地震,因为支那没有地震而感到异常恐怖,他们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略)
(朱弘译注:当年的“支那”并不是贬义词。)
然后,我从传通院(寺庙)前经过高田马场走回家去。途中碰到了自警团或者退伍军人或者本地人士——他们每隔二、三个街区就设岗置哨盘查行人,戒备森严,我在回家途中遭到了二十七次搜身检查,每次都要讲明情况才能通过岗哨。终于走回自己的家,时间已是早上五点半左右了。(略)
(9月2日)
(略)
随后,我独自一人花费两个半小时走回自己的家。途中亦是骚乱纷纷,因为青年团的盘查相当恐惧,你不得不担心自己可能被误解成朝鲜人!所幸中途可以造访小石川/林町的朋友,从他家里借到了灯笼、蜡烛和火柴,我便沿着昨夜的路径往回走。果然,每隔二、三个街区就有一个关卡,我随时都要接受盘问。经过户塚町的时候,蜡烛烧完灯笼黑了。结果当我走到某个自警团的关卡被对方搜身,他们发现了我口袋里的火柴,问道“你小子拿着火柴干什么?!”我解释说:需要借灯笼也需要带着它点燃蜡烛。但他们毫不讲理:“你小子莫非要拿它放火吧!你莫不是朝鲜人吧!”我只好辩解说你们不妨看看我的长相就明白了嘛,但这简直就像对牛弹琴。幸亏其中有人说了一句:“这家伙是日本人”,我才终于得以过关。记得自己回到家里,时间已过了夜里十一点钟。这一夜我心烦意乱,始终盘算着救护支那学生的计划或者***运动的方式而无法安眠,眼睁睁地等到了天亮。(略)
(9月4日)
第二天也就是9月4日,我所居住的上落合方面也聚集了什么自警团什么退伍军人团之类的,他们煽动说朝鲜人来袭朝鲜人放火朝鲜人往井里投毒,他们彻夜轮班负责这一带的警戒。此时我已听到不少消息,说是日本人也有被误伤的、或是日本学生被误解成朝鲜学生而遭到伤害等等。由于支那学生的日语还不熟练,他们同样可能被误会为朝鲜人而遭受危害,想到这里我就格外担心。因为地震以来积累下的疲劳,9月3日我整天休息在家不曾外出,那么现在已经刻不容缓了!今早,我七点就出了门,首先就本学会的房屋烧塌了的问题、以及为了汇报自己9月1、2两日的行动,我造访了青山**町六丁目白岩龙平(本会理事)的家,然后前往外务省。接着我又去了麹町**本町的日本石油公司,再次造访***氏,就自己地震以来所做的事情逐一做了汇报。另外也去了**氏的家,但他不在。此君和江口、白岩三位都是本会理事,创业以来非常尽力,并对本会遭受的震災十分担忧。**氏对我的汇报表示很满意。最后,当我来到被大火烧过的神田桥一带,但它已被烧掉了半边,我好不容易从附近的水道桥上走过去。再走到本乡的追分町,抵达日华学会第一、第二学生寮的时候,正好下午二点钟。
地震当天晚上,当我探望学生寮的时候,尽管**跑出去避难而没留下一个人,尽管余震时时发生,但这里还有**,餐具、食物之类的也放在宿舍里,因而一名舎監和五、六名学生、以及管食堂的森大妈的一名下人还留在那里。我今天造访的目的,一来是要了解这两天学生们都有什么变化,二来也是想调查一下避难所的情况。哪知道,督管学生的森大妈的女儿静子慌慌张张跑过来:“大事不好,请您赶紧去看看我母亲!”
一问才知道,原来日华学会第一宿舍的学生们先是跑到巢鸭中学避难,等到要回宿舍,却在位于本乡的肴町和追分町中间位置的电车站附近碰上了拉起警戒线的自警团,盘问“你们是不是朝鲜人?”一位学生强硬地辩解道:“我们是支那人决不是朝鮮人,你们不要搞错!”可那时民众已经情绪激昂,再加上这边的日语表达又不是那么准确,怎么解释对方也不理睬。当一个人觉得学生们可疑,说他们是朝鲜人的时候,这话传开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就叫嚷起来:“啊,朝鲜人来了,干掉他们!”于是一帮手抓棍棒、铁棒、猎枪、长矛和大刀的家伙就冲了过来,最终把四名学生和带领他们的一位老太太(朱弘译注:根据前后文分析,很可能就是森大妈)围在中间。冲在前排的还在盘问说“你们究竟是不是朝鲜人!”的时候,围在后面的却大叫起来:“干掉他们!收拾他们!”纷乱之中,长矛刺了进来大刀也砍将上来。老太太见势不妙,赶紧跪在地下向大家哀求:“这都是寄宿在第二中华学舍的支那留学生,是日华学会负责照管的。他们绝对不是朝鲜人,你们可要千万核实啊!要是伤害了他们,我这可就麻烦大啦!”但是群众哪里肯听她的话,反而骂道“你这混蛋!竟敢偏袒朝鲜人,那就连你也一道不客气了!”而不明就里的人们还在往前涌,如同瞄准了猎物一般张牙舞爪。老太太正大声连呼救人、救人啊,群众里面一个手执大铁锤的——照着她的左膀就砸了下来。老人家顿时血流不止,但却依旧哀求大家不要动武。
但这哀求根本没用,被围在人堆里的四名学生眼睁睁地就被扯散开来,有被拽到这边的有被拖到那边的。其中的两个,好不容易才挣脱出来逃回了追分町的学生寮,而剩下的那两个立刻就受了伤,老太太也被铁锤砸中了。因为他们都血流不止,追分町的青年団上来帮了忙,把几人带到根津町日本医科专门学校的医院进行了急救。所幸,两名学生和老太太虽然出血挺多,但都还不算重伤,只是缠上了临时绷带。
我正听着,老太太和两名学生回来了,又把当时的情况大致讲了一遍。可这两名学生却又告诉我,还有两人可能早就遭到毒手甚至已不在人世了!这下子闹得我心慌意乱坐立不安,只想立刻赶去查明真相。于是,把当时的情况逐一问了明白,再把今后的安排一一交代给了在场的职员,我随即单独出发,赶往事发现场的肴町附近。
肴町的车站附近简直是鮮血淋漓惨不忍睹。我正寻思着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呢,就望见对面走来了一些人,是追分町和肴町一带的青年团,用门板抬着一个伤员。我跑上前赶紧查看,正是据说出事了的两名留学生中的一个,名叫姜(音译,或许姓韩?)**。于是我索性助上一臂之力,伴随青年团争分夺秒往前赶,终于把担架抬进了日本医专附属医院。这里汇集了一大堆震災伤员以及也在等着急诊的伤患病人,我由此断定这个学生不可能得到完好的治疗,但因为附近实在找不到第二家像样的医院了,也只好请求医生赶紧先给他治了再说。医生无奈地告诉我:这里已经容不下伤员了,你还是想办法去别的医院吧。我则拼命地恳求对方,我说这是支那留学生,伤重到这个程度,假如耽误了抢救今后可就麻烦了,请千万看在他是外国人的情面、也请站在国家的角度上,无论如何马上抢救一下吧!
万幸!我的祈求成功了,他被送进了手术室。
可是这学生被伤得实在太惨了,据说他的头部、背后、手足遭到了刀砍、枪刺、棍殴,手术起来很麻烦。更兼失血过多,医生对我讲:全面治愈看来是不可能了,先留下观察一夜再说吧,我们反正尽力而为。
而这个受伤的学生呢,嘴里只说了些“遗憾啊太遗憾了!”之类的话,我们正担忧他会不会精神异常呢,但似乎只是情绪过于亢奋而已。
因为还要寻找另一个下落不明的学生,我把万事托付给长良院长,离开医院就直奔追分町的青年团事务所。我对他们说:得到你们关照的那个伤员是支那留学生,人已经被送进了医院,但还有一个不知逃到了哪里、也不知被伤害到何种程度,无论如何请大家再帮忙寻找寻找!他们一片好心,说是愿意帮着寻找。于是,我确认了一番以后,直接就跑到管辖肴町一带的駒込警察署,向署长一五一十地介绍了悲惨的现状。我恳求署长:“事态严重,希望无论如何要对支那学生进行救护!而下落不明的另一个则很可能也遭了毒手,所以请一定要找到他,并赶紧向警视厅做详细汇报,千万不能在外国留学生身上再发生如此悲剧!请您们拿出对应的方案吧。”
哪知道警察署长的回答却是:我们这边按理应该尽力而为,但如此混乱之际人手实在有限。何况,就算是救助了支那留学生,可老百姓却可能误会我们保护的是朝鲜人,谣言千里啊。就在你来之前,很多群众就包围了我们,他们大叫“交出朝鲜人!要是不交出来,一把火烧了你们警察局!”等等。所以你看,就算是有这个心,你说的这个学生***,我们恐怕也很难给予他最好的援助。当然啦,我们自然会尽力而为的。
向駒込警察署提出了救援请求,我正想返回追分町(中华学舍)方面呢,负了伤的森妈妈却赶过来给我传话:下落不明的学生找到了!他姓陈,幸运地躲进了的一家支那料理店,身上也没受伤。原来,他也同时遭到袭击,并且被一把铁锤打中了头顶。但是万幸,他当时戴了一顶厚厚的草帽,帽子坏了脑袋倒是保住了!又因陈君的外貌和日本人并无大异,所以群众也没注意到他(的溜走)。据说陈君用纸包了自己的帽子,想把它留作永久的纪念。
接下来,我和一个名叫三轮的职员再次前往医院,询问自己离开的这一个来小时中、伤员治疗的情况。但是,他已被缠上应急绷带送回病房了。“疼啊,疼啊,”他的声音如同梦呓,但看上去情绪却是渐渐平静了。医生告诉我:照这个样子,如果不发高烧,今晚他或许能挺得过去,但希望你们做好思想准备,他九成九是难以治愈的,等等。
(略)
(9月5日)
地震发生以来一到四日,东京市内完全看不到人力车,而自行车也轻易租借不到。如今体力已近不支,只好四下派人寻觅,终于找来一台人力车,我便乘车拜访住在市区外西大久保的(外务省)亚洲局出渕(胜次)局長。由于我登门的时间过早,他好像吃惊不小,但我赶紧解释:因为发生了必须直接陈述的重大问题,所以必须尽早跟您见面!于是,亚洲局长很痛快地就立刻接见了我。
我对他详细叙述了地震以来自己亲历的一切,告诉他“如果对这种状态不加干涉的话,那么千百名支那留学生就将陷于悲惨的境地。到那个时候,这不仅将成为国际性的灾难,它还意味着日本人在重大关头丧失节度,由此关涉日本作为国家的信誉。所以事态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所以,请求他做出应急的处置方案。
出渕局長不仅热心地听完了我的话,甚至表示这也是自己身为亚洲局长必须尽力的职责之一。“你能这么快地赶来汇报情况,真是太好了!现在,必须马上全力以赴救护学生,而你也最好参与进来。当下最重要的,是光靠警察的力量保障不了東京市内外的治安,必须发布(军事)戒严令,依靠戒严司令部的力量拿出应急措施。我因为今早十点要去外务省,而情况又那么紧急,希望你替我走一趟,先去戒严司令部访问福田(雅太郎)大将,告诉他有要事相商。”说着,他就给我写了一份介绍状。
拿上亚洲局长的信件,我直奔位于参谋本部的戒严司令部。可由于时间还是早上八点前后,我没法见到福田大将或者原少将(朱弘译注:这里的原姓少将可能有误,戒严司令部当时似乎只有一个少将:参谋长阿部信行),但总算见到了山下少佐,递交了外务省亚洲局出渕局長的介绍状。因为本来就认识这位山下少佐,所以我事无巨细讲得很彻底,希望他赶紧通知有关部门——拿出保护支那留学生的方案。告辞之前,我拜托他向福田司令官转达本次造访的目的。接着,我又直奔内务省(朱弘译注:内务省下辖警视厅)拜访田中内务次官,向他陈述了自己对亚洲局长谈过的同样内容。
最后,我在十点前赶到了外务省。已经上班的出渕局長叫来他的部下,和我一起商讨种种救援方案。当局長希望我提议“如何进行救护”的时候,我是这样说的:“首先需要一笔钱——用它来租用汽车、购买自行车、聘请临时人员——前去访问散落各地的支那学生,将他们从危险地带集中收容。总之不能让他们处于分散的境地,那么提供生活保障是必不可缺的。其次,假定东京圈内有一千三百名支那留学生,再假定其中的五百人——他们要么安全上没有问题、要么业已归国而不在日本——那么就算以七百人为基数、每人救护费用以五十日元计算,需要支出的总额是三万五千日元。”
对我的这项提案,出渕局長表明了相当的诚意:“需要用钱的地方,你大可不必在意,外务省自然会补足这笔开支。你就只管去琢磨并做好你那些救援方案吧,你办不成的那些事,外务省可以代劳。”(略)
(以下是当年“日华学会”发布的第一回传单的内容:
关于中华民国留学生的救护
收容罹难学生
収容所为本乡第*高等学校***寮
食物需求者,可在日华学会定量领取
帮助旅行和归国学生斡旋船票
为旅行者办理相关的保护手续
伤病学生的救护
相关的其他罹災保护措施
上述事项,均在日华学会事物所办理
本乡駒込追分町31番地第二中华学舎内 日华学会)